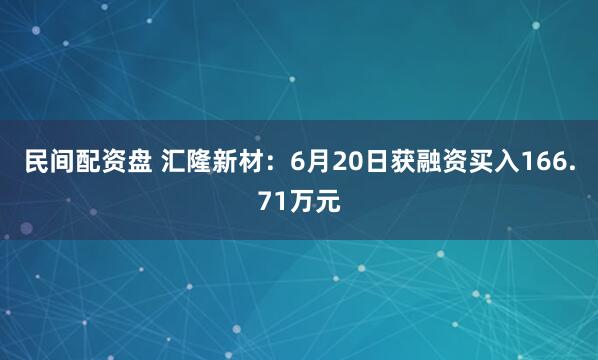《牺牲》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定格在54岁,仅凭借七部长片,就奠定了他在电影艺术史上不可撼动的传奇地位。
《殉道学》一书汇集了塔可夫斯基从38岁直到临终的全部日记。1970年到1986年,不仅凝缩了一位伟大导演创作生涯的黄金年代,也跨越了世界电影的十字路口。
书中的日记文本始自1970年。这一年,次子安德留什卡出生,塔可夫斯基和妻子拉丽莎在距莫斯科300公里的米亚斯诺耶买下了一栋别墅,从借住的岳母家搬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住所。
同年,影片《飞向太空》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启动制作。房屋的翻新和扩建与拍摄项目同步开展,大量草图穿插在日记文本之中,别墅的空间结构与陈列细节在电影布景中一一复现,两者形成了奇妙的互文。
影片里,凯尔文在外太空沉湎于记忆的幻象,现实中,塔可夫斯基开始借日记造访童年时光,行文之间,梦境与回忆频频浮现。
展开剩余91%此后十年间,世界电影在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下反复经历着融合与裂变。
法国电影新浪潮与后现代主义狭路相逢,开启了对欧洲文化传统的颠覆之路;日本电影经历战后社会的反思和迷惘,重新拷问道德与人性;好莱坞制片工业借资本之力变革重生,随美国霸权时代的来临走向繁荣。
塔可夫斯基则用《镜子》和《潜行者》开创了苏联电影制片体制的诸多先河,使得电影艺术跨越了意识形态分野和政治感召诉求,明确了自身所能抵达的哲学深度。
1.
“爱是将自己作为礼物献给他人”
塔可夫斯基一生从未停止对自我与他人的探索,从未中断用镜头捕捉世界不可见的轮廓。每一部影片都是他对外界感知的真实呈现,而他的感受与思考并未止步于银幕,日记还原了生活本身更为波折起伏的样貌。
《伊万的童年》
对凡俗日常的深入观察造就了这位天才导演敏锐的直觉和犀利的目光。在塔可夫斯基早期的记述中,随处可见对制片厂领导、业内同行甚至亲友挚交的尖锐评述,他与大多数合作伙伴之间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隔阂。
《安德烈·卢布廖夫》剧本的合著者、苏联导演冈察洛夫斯基曾在晚年采访中回忆塔可夫斯基:“年轻时,安德烈是个强势的人,我想是因为他很脆弱。”
《伊万的童年》主人公、《卢布廖夫》里钟匠儿子的饰演者布尔利亚耶夫也曾公开坦言:“那个时候我很尊敬塔可夫斯基,但也很难理解他。他说过,演员对他而言只是花钱雇佣的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塔可夫斯基愈发显露出性格里柔和与开放的一面。在远离故土之后,世界在他眼中重新变得扑朔迷离,他人在他笔下再度回归神秘的存在。
“我越来越觉得人类是个谜。我的逻辑和评价体系正在瓦解,无法再对别人作出判断。”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对他人的严苛审视逐渐被理解和宽容取代,以往与合作伙伴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也慢慢扭转。
1972年,在《镜子》拍摄期间,塔可夫斯基曾与合作多年的摄影师瓦季姆·尤索夫因创作理念不合分道扬镳:“他毕竟是个凡俗之辈,我在电影中谈论我自己,他对此满腹怨气。”
直到1983年,两人在米兰再度偶遇,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详述了两位游子异乡重逢后惺惺相惜的情愫:“分别时我们有点儿伤感,好像彼此都明白,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1984年,在瑞典拍摄《牺牲》期间,塔可夫斯基与摄影师斯文·尼科维斯特相识。初次合作,彼此之间就建立起了工作范畴之外的情感共鸣。在得知斯文经历的丧子之痛后,塔可夫斯基写道:“我感觉斯文很孤独……他身边没有朋友。我很想有他这样的朋友。”
早年经历的婚姻变故让塔可夫斯基得以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察觉出父亲与母亲分别多年后仍然存在的微妙羁绊。
《镜子》著名的开篇——女主人公坐在房前篱笆上凝视远方的镜头——再现了塔可夫斯基童年的回忆,却是通过他成年后的视角:“那个时候,妈妈不知道父亲是否还会回来,她从未说过,但她一直在等。”
《镜子》
安德留什卡出生后,塔可夫斯基以近乎补偿的姿态,将所有包容与爱护全数倾注在了小儿子身上。
在197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塔可夫斯基写道:“爱是为了一个人,或为了自己而抛弃另一个人。它的本质是冲突。”
此时正值塔可夫斯基排演《哈姆雷特》,也是《乡愁》剧本构思之始。这一段对爱的定义,衍生出此后影片里戈尔恰科夫和叶甫根尼娅在酒店房间的争执,以及叶甫根尼娅饱含愤怒与怜悯的独白。
人类对幸福的追寻、对信仰的实践在塔可夫斯基的每一部影片中也有着多样的呈现,对于不同表达方式的求索轨迹在他的日记中同样可以窥见端倪。
1979年1月28日,在为《潜行者》构思的续集中,塔可夫斯基让潜行者成为了法西斯,强迫人们进入房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被迫去幸福’ ——在种种通往幸福的道路中,有没有这样一条?”
而《乡愁》的剧本在开机之前便经历了数个版本的修改,在尝试为故事先后撰写过不同结局之后,塔可夫斯基最终让戈尔恰科夫点燃了多米尼克的蜡烛,用8分45秒的长镜头,护送摇曳的烛火涉渡了彼岸。
《乡愁》
离世前几个月,塔可夫斯基开始重新阅读福音书,重新审视哈姆雷特和他的复仇。他的文字越过欲望、背叛和仇恨,执着地讲述着信仰、牺牲与爱。
1986年8月于德国疗养期间,他在日记里重新界定了“牺牲”的含义,也借此串联起自己几乎所有影片的主题:“归根结底,这(牺牲)是找不到出口的爱——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情欲,而是精神之爱。爱是将自己作为礼物献给他人。”
2.
“我永远看不到的家”
1932年,塔可夫斯基出生在伊万诺沃州的小镇札弗洛塞,在父母分别之后,他和妹妹曾随母亲短暂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间小公寓里。
随着战争的爆发,一家人离开莫斯科,前往伏尔加河畔的村庄尤里耶维茨,塔可夫斯基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岁月。
1955-1957年,高尔基大坝和下游水电站开工建设,札弗洛塞及周边村庄被洪水淹没。村庄居民迁居附近的山上,但塔可夫斯基出生的房子随大坝开闸沉入水底,连凭吊之地都不复存在。
屋中如骤雨般倾泻的水流成为了《镜子》中最富诗意的一幕,那曾是纠缠塔可夫斯基多年的梦魇,是他沉入水底的家。
而战时他和妹妹玛丽娜度过童年的村庄,同样难逃消失的命运——随着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热潮,记忆里的沙丘和林荫路早已被大楼和堤坝取代。
1973年12月8日,为筹备《镜子》的拍摄,塔可夫斯基前往尤里耶维茨堪景,归来后他满怀忧伤,在日记里写道:“人不该回到失落的土地……我用电影埋葬了自己的故乡。”
《镜子》
即便在成年之后,塔可夫斯基营造居所的努力也充满了坎坷与变故。1970年十月,米亚斯诺耶刚修缮好的房屋遭遇火灾,主体结构烧毁。
在日记里,塔可夫斯基用短短的一段文字记录了房屋失火后的情况,直到多年后的访谈中,才提起这一事件给他带来的难以磨灭的痛楚:“我躲得远远的,不敢回去看,我害怕看到烧焦的废墟。”而烈火中的房屋,这一幕被他回避的残酷景象,此后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影片里重现。
人与所居之地的羁绊几乎贯穿了塔可夫斯基的每一部影片,从《伊万的童年》里被战火焚毁的村庄,《安德烈·卢布廖夫》在修道院壁画中找寻归宿的圣像画家,《飞向太空》里索拉里斯为凯尔文营造的旧居幻象,到《乡愁》教堂废墟中的俄罗斯乡舍和《牺牲》里亚历山大烧毁的海边小屋,都在讲述一个相同的故事。
而塔可夫斯基本人先后辗转莫斯科、罗马、柏林、佛罗伦萨和巴黎,不停地修建、改造和装饰一处又一处居所,却从未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和他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塔可夫斯基毕生都是一位漂泊者。对故土的思念、对信仰的追寻和对家的渴望,三者始终相互缠绕,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执念。
1984-1985年间,塔可夫斯基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拍摄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牺牲》,最终选择了荒凉粗粝的哥特兰岛海岸作为拍摄地,因为这里有着与俄罗斯乡村一样的空旷与贫瘠,弥漫着宛若故乡的朦胧雾气和忧郁氛围。
在影片筹备期间,塔可夫斯基曾花费数日寻访一座始建于12世纪的东正教堂,最终却抱憾而归。在拍摄地附近留下的记录影像里,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延伸至波罗的海,唯独少了让他魂牵梦绕的修道院轮廓。
1984年11月8日,塔可夫斯基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做了个让人心碎的梦。我又梦到俄罗斯北方的一片湖泊,天刚破晓,湖对岸的两座东正教修道院在晨曦中伫立,教堂和院墙美丽非凡。醒来后我悲伤难耐,心里一片凄凉。”
《牺牲》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未完成的故事构思与剧本创作,塔可夫斯基最深的牵挂是他建造中的房屋。
1983年,他曾在意大利的圣格雷戈里奥看中了一处古老的宅院,准备对其翻新重建,但改造方案始终未获政府批准。1985年,他和拉丽莎在罗卡尔贝尼购置了一处土地,计划移民后于此定居。不久之后,塔可夫斯基被查出肺癌晚期,直到临终前,房屋的建设方案仍未敲定。
在放化疗间隙,塔可夫斯基仍在和设计师反复沟通,不断修改建筑设计图纸。最后一篇日记的结尾,附有一张塔可夫斯基亲手绘制的草图,在图片上方,他用癌症末期饱受疼痛折磨的双手写下一行颤抖的字迹:“我永远看不到的家”。
让人心碎的笔触讲述着一个伟大灵魂与他深深眷恋的世界逐渐失去连接的哀愁,也倾诉着一个脆弱个体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终究没能抵达的和解。
3.
“我们逝去后的灵魂会怀念这人世间”
如果电影承载的是塔可夫斯基生命深处的热望和忧伤,《殉道学》记录的则是他现实生活里真切的期盼与悲怆。
从好友帕拉杰诺夫因政治立场入狱、演员索洛尼岑受片场核辐射影响患病离世,到银幕内外的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国家政权更迭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塔可夫斯基所记载的十七年生命历程中,处处回响着漫长人类历史踏过二十世纪的苍茫足音,字字映现出百年光阴投射在渺小个体身上的斑驳暗影。
如同他的镜头一样,塔可夫斯基笔下也少有恢弘自洽的时代叙事,他永远专注于描摹个人生命里隐秘的裂隙,描摹从裂隙中闪现的生命深处的幽暗与光辉。
他的日记构建了一处个体生命经验与社会政治变迁交融的独特地带,奇迹般地定格了历史钟表停摆的瞬间——那是权力与资本无法抵达之处。
正是这一处空间,让他在苏联生活时得以躲避政权凌驾于个体之上的严酷与冷峻,也让他在移居西方后得以反观无限扩张的资本对道德秩序的碾压,窥探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在人类身上遗留的伤口。
塔可夫斯基,《镜子》勘景现场
在生活日常、工作笔记和哲学思考之外,塔可夫斯基还在日记里描绘了自身经历的超验时刻。
那些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伟大灵魂屡屡现身他的梦境之中,在亡故后与他诚挚交谈。他的书写似乎具备对抗现实规则与时间秩序的力量,拓刻着生者和逝者从未言说的挚爱与离愁。这些文字有着带领观看者穿梭两个世界的奇迹般的本领,如同一卷现实与幻象、当下与回忆、生命与死亡相互映衬的底片。
影片《镜子》中有一个场景,主人公躺在病床上,手里握着一只纤弱的小鸟,在弥留之际张开手掌放它飞走。出演这一幕的不是主人公的饰演者扬科夫斯基,而是导演自己。
在《殉道学》的结尾,收录了一张塔可夫斯基临终前的照片,他身处巴黎去世的那间病房,一只小鸟站立在他手上——《镜子》里被他放飞的小鸟,穿越了此后十三年的光阴,降落在了他生命的尽头。
《镜子》
毫无疑问,塔可夫斯基创作的影像容纳了他本人,在每一次被观看的时刻,他的思维和情感都会被再度创造出来,在观看者的意识深处全盘浮现。
如果在银幕前,你曾感受过超越自身经验的热烈爱意和深沉悲悯,曾被不明就里的苦涩或幸福击中,在阅读《殉道学》时,你会逐一找到答案。
在回忆与已故友人阿赫玛托娃的对话时,塔可夫斯基写道:“我明白为什么我们逝去的灵魂会怀念这人世间。”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塔可夫斯基也在怀念这个世界。每当他写下的字句被崭新的目光阅读,他都会再一次讲述他的怀念,讲述让他懊悔和眷恋的往昔。
在迎接这些文字的时刻,你能触摸到来自他灵魂深处的喜悦与疼痛,它们如此真实、如此有力,甚至为你的一部分生命也赋予了重量。你知道你此后的生命将携带着这份重量,在你看向世界的眼睛里,从此蕴含着他的目光。
📹 ⚫️
塔可夫斯基日记《殉道学》
现已上线“多抓鱼”
理想国
撰文:刘馨浓
封面图:《镜子》
商业合作:bd@vistopia.com.cn
投稿或其他事宜:linl@vistopia.com.cn配资广告
发布于:北京市富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